編注:本文係十架路出版社「五種迷思」(5 Myths)系列文章之一。「迷思」的英文爲myth,或譯「誤解」,即「常被信以爲真,但實際上是錯誤的觀念」。
請允許我先介紹與伽利略同時代的保羅·薩爾皮(Paolo Sarpi)。威尼斯人保羅·薩爾皮(1552-1623)的著作深受新教徒的喜愛,他曾經是伽利略的朋友。薩爾皮最偉大的作品是《天特會議史》(Istoria del Concilio Tridentino)。這部鉅著使他成爲意大利反改教運動最強大的對手。
爲什麼要召開天特會議?正如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所指出的 [1]:
十六世紀初,許多人熱切盼望召開教會大公會議,以解決天主教和改教家之間的分歧……關於大公會議的職能,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觀念:一方認爲新教徒應派代表參加會議,並應在聖靈的指導下達成一項方案,從而恢復教會的合一;另一方則拒絕考慮向改教家讓步,而專注於在教皇的領導下實行更加嚴格的治理。
結果,天特會議成爲了反改教運動的憲章。耶茨說 [2]:
薩爾皮間接地指出,如果在天特會議上採取了正確的路線,那麼整個教會將會在某種程度上按照英國聖公會改革的模式進行改革(神職人員可以結婚、主餐時餅酒兼領和用本地語言進行禮拜都是英國聖公會的特色)。但是,會議選擇了錯誤的方針,教會非但沒有改革,反而因教皇的新僭越行爲而偏離正道。
作家戴維·伍頓(David Wootton)的反思如下 [3]:
薩爾皮精心介紹了所有關於教會改革的建議,並剖析了神學家們相互衝突的觀點……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傳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真正的大公會議應高於教皇,大公會議應自行決定議程,而不是由教皇代表強加給它,其法令不應依賴於教皇的批准 。
伍頓指出,薩爾皮認爲天特會議是「一場希望和期待落空、腐敗和濫用權力得逞的悲劇」。伏爾泰(Voltaire)引用了薩爾皮對天特會議的如下看法 [4]:
終於我們有了偉大的天特會議——但教條是無可爭議的,因爲(根據)保羅·薩爾皮修士的說法,聖靈每週通過郵件從羅馬來到天特,只是保羅·薩爾皮修士有點接近異端。
稱薩爾皮爲「偉大的揭露者」,伍頓寫道,天主教歷史學家胡貝特·耶丁(Hubert Jedin)將薩爾皮描述爲「繼路德之後教廷最大的敵人」。
薩爾皮的著作引發了強烈的仇恨, 1607年10月5日,薩爾皮遇刺,身上有十五處匕首造成的傷口,奄奄一息的他後來倖存下來。亞歷山大·羅伯遜(Alexander Robertson)接著講述了這個故事 [5]:
(薩爾皮)並不經常提到他的敵人,但他有一兩句話流傳了下來。外科醫生阿誇彭登特(Acquapendente)在探查最嚴重的傷口時,詳細描述了傷口的 "stravaganza"(粗糙),保羅修士說:「然而,世人卻說這是按照 '羅馬教廷的風格' 做的。」
天特會議確定教會是聖經的最終解釋者,並承認聖經和教會傳統具有同等權威。伽利略寫道:「嚴謹睿智的神學家的職責是解釋經文,」他肯定了教會是最終解釋者的觀點,並敦促在解釋經文時不偏不倚。相比之下,我們更強調聖靈通過聖經向人啓示神,而不太強調通過 「嚴肅睿智的神學家」來解釋經文。天特會議的決定將對科學研究產生嚴重影響。
保羅·薩爾皮也是一位實驗科學家,哥白尼體系的支持者,也是伽利略的老朋友。他在威尼斯共和國望遠鏡的發展和完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絕不應被低估。
1609 年 7 月,我們的故事從荷蘭望遠鏡的發明轉到了威尼斯共和國。這個插曲的關鍵人物是威尼斯人保羅·薩爾皮。在《伽利略的望遠鏡》(Galileo's Telescope)一書中,作者馬西莫·布坎蒂尼(Massimo Bucciantini)、米歇爾·卡梅羅塔(Michele Camerota)和弗朗科·朱迪斯(Franco Giudice)對薩爾皮做了如下介紹 [6]:
這就是讓我們深感興趣的薩爾皮:1606-1607 年他直接導演和推行了反對教皇禁令;1619 年他寫下了《天特會議史》,成了千夫所指之人。然而,在他全身心投入歷史和政治之前,他潛心探討科學問題,注定要在望遠鏡的問題中發揮關鍵作用。然而在望遠鏡歷史研究中,專家往往低估了他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忽視了他。
當時,威尼斯共和國與教皇發生衝突,薩爾皮堅決反對教皇插手國家事務。早在 1608 年 11 月,薩爾皮就獲悉了關於望遠鏡的消息。當時,這只是一個傳言;他沒有樣品,無法研究望遠鏡的祕密。第二年,望遠鏡現身威尼斯。1609 年 7 月 21 日,薩爾皮寫下了這段話 [7]:
望遠鏡可以讓遠處的事物清晰可見。我非常喜歡它,這項發明美輪美奐,工藝精湛,但我發現它毫無軍事價值,無論是在陸地上還是在海上。
很快,祕密就被揭開了 [8]:
由於工匠大師們立即意識到有錢可賺,盒裝望遠鏡或長筒望遠鏡成了公開的祕密,在許多城市都能買到,這不僅證明了其流傳之廣泛,也證明了其質量之低劣:
關鍵就在這裡:鏡片質量很差,但儀器本身的概念卻非常新穎。
薩爾皮是伽利略的科學對話者。但伽利略要製造自己的望遠鏡,時間至關重要。我們讀到 [9]:
1609年9月22日至29日的那一週對於伽利略來說是命運的轉折點。這不僅標誌著他成爲一個備受歐洲推崇追捧的鏡片製造商,也意味著他開始了新的生活。在46歲時,他即將見證自己的人生會發生巨大變化。荷蘭望遠鏡日益完美,伽利略將望遠鏡改用作天文儀器這一舉措將徹底改變他的日常工作……城裡人成天聊的就是此事。
1609 年 8 月 24 日,伽利略向威尼斯議會展示了一個望遠鏡;鏡筒長約六十釐米,直徑四十二毫米,放大倍數爲八倍。大家都「議論紛紛」,認爲伽利略的望遠鏡在質量上大大超過了荷蘭研製的望遠鏡。我們不知道伽利略是什麼時候開始研製他的第一個望遠鏡。但我們的確知道,薩爾皮不僅對望遠鏡非常了解,而且還積極參與了製造,從他 1610 年 3 月 16 日的信中可以看到這點。
保拉·芬德倫(Paula Findlen)詳細寫道:「薩爾皮利用他廣泛的政治網絡收集望遠鏡的消息;他經常與伽利略一起出現,討論技術問題,尋找最好的工匠和材料,並一起觀測天空」(強調爲作者所加,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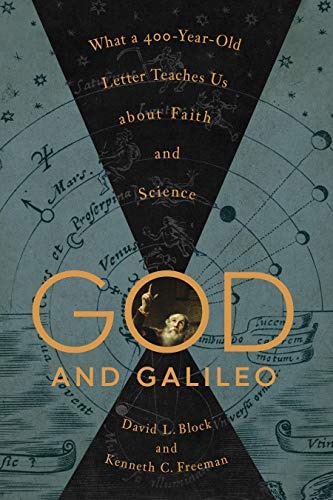 1610 年 3 月 13 日,標誌現代天文學誕生的里程碑事件發生了:伽利略在威尼斯出版了傳奇著作《星際信使》(Sidereus Nuncius)。這是伽利略根據其望遠鏡觀測結果發表的第一部科學著作,論文中包含了伽利略早期觀測到的山形月亮、銀河系中肉眼無法觀測到的無數恆星以及圍繞木星運行的四顆麥地奇行星。
1610 年 3 月 13 日,標誌現代天文學誕生的里程碑事件發生了:伽利略在威尼斯出版了傳奇著作《星際信使》(Sidereus Nuncius)。這是伽利略根據其望遠鏡觀測結果發表的第一部科學著作,論文中包含了伽利略早期觀測到的山形月亮、銀河系中肉眼無法觀測到的無數恆星以及圍繞木星運行的四顆麥地奇行星。
1610 年 3 月 16 日,《星際信使》出版僅三天後,薩爾皮寫信給雅克·萊沙西埃(Jacques Leschassier),信中提到了薩爾皮製作的望遠鏡。這封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10]:
如你所知,這臺儀器由兩個透鏡(你稱之爲月鏡)組成,它們都是球面的,一個凸面,另一個凹面。我們(薩爾皮和他的助手)用直徑爲六英尺的球體作了一個,用直徑小一點的另一個球體作了第二個。
現在,我們來談談策略和疑問。在《星際使者》中,伽利略寫到觀測所用的望遠鏡之歷史時,所有功勞都歸於他本人,一點都沒有被提到薩爾皮。
伽利略認爲自己一人獨立完善了望遠鏡,他不願意讓任何人與他分享這名譽。他顯然是想讓大家覺得自己是獨自一人製造出這種儀器的,但這不符合事實。布坎蒂尼、卡梅羅塔和朱迪斯在此提供了寶貴的見解。伽利略的省略顯而易見,三位作者也謹慎地指出了這一點:「《星際使者》這部作品裡有許多刻意遺漏的東西……當我們冷靜地閱讀這部作品時,可以說是在代表威尼斯(ex parte veneta)閱讀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同樣的、系統性的刻意隱藏人物、文字和事件的手法」。
在這裡,我們發現伽利略背棄了與他「分享了近二十年關於自然和人類的無盡對話」的薩爾皮。難道薩爾皮不是伽利略在帕多瓦時最親密的科學對話者嗎?正如布坎蒂尼、卡梅羅塔和朱迪斯所說的,這轉折多麼戲劇性啊。「毫無疑問,薩爾皮及其助手的合作是決定性的,儘管伽利略從未公開承認這一點」。
總而言之,威尼斯人保羅·薩爾皮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1]:
他在聖瑪麗亞·德·塞爾維修道院進行天體觀測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事實上,望遠鏡的歷史並不是沿著單一的矢量或單向的路徑發展的,而是正如威尼斯所展示的那樣,是一個人類和知識重重疊疊組成的群島:爲了恢復原樣就必須同時講述的一個群體故事。
個性和目的有時會推動科學成果,而成果的產生過程也並非總是客觀的。在伽利略的一生中,有些神職人員炫耀自己的榮譽,天文學史上也不例外,照樣充斥著許多追求第一並獲得殊榮的例子。僅僅爲了個人原因而踐踏同行是一種犯罪。此刻,我們想起了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的一首小詩 [12]:
萬罪之中,最惡的是竊取榮耀,
甚至比盜墓更受詛咒。
伽利略時代的教會有一個議程,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維護教會的權力。他們的勢力無所不在,甚至在科學問題上也是如此。權力遊戲和伽利略反對者的個人利益佔了上風。
伽利略認識到,科學真理存在於觀察者之外,觀察者沒有能力使事物變得真實或虛假。自然之書超越了人類的力量:個人無法影響繞木星運行的行星,也無法影響太陽表面的黑點。伽利略說:「任何被造物都無法無視其自身的性質所決定的事實,使(命題)爲真或爲假」。儘管天文學有許多沒有問答的問題,但大自然這本打開的書之奇妙在於它的透明。人類竟然可以「指示」上帝如何創造宇宙,這簡直超乎想像。正如泰戈爾(Tagore)之前所說:「螢火蟲對星星說,『有學問的人說,你們的光芒總有一天會消失』。星星沒有回答」。大多數問題都有答案,伽利略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真理就在那裡,只要我們去尋找,就一定能找到。
伽利略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個人議程和個人利益。許多讀者可能會認爲,今天的科學問題已經不涉及個人利益,但事實並非如此!
薩爾皮在兩次未遂暗殺中倖免於難,最後他死於 1623 年 1 月 15 日。關於薩爾皮的地位,我們可以用羅伯遜的話來概述 [13]:
在天文學領域,伽利略稱他爲「我的父親、我的大師」。作爲數學家...... 「在數學科學知識方面,歐洲沒有人超過保羅·薩爾皮大師」。
還有更多的讚譽 [14]:
帕多瓦著名外科醫生阿誇彭登特(Acquapendente)稱他爲「本世紀的神諭」。作爲一名磁力學家,那不勒斯的德拉·波爾塔(della Porta of Naples)和科爾切斯特的吉爾伯特(Gilbert of Colchester)都承認他的學識,前者說:「我絲毫不感到難爲情,而是很榮幸地承認,我從保羅修士那裡學到了許多關於磁力現象的知識,他不僅是威尼斯,也是意大利乃至全世界真正的光之飾品。」
對於這樣一位具有洞察力和地位的人來說,他死後會被賦予怎樣的尊嚴呢?亞歷山大·羅伯遜博士(Alexander Robertson D.D.)爲我們描述了這樣一番情景 [15]:
兩百多年來,他(薩爾皮)的遺體沒有找到一個安全的安息之地,爲躲避敵人如狼似虎的追捕,只能被砌在牆壁和祭壇後面,藏在私人住宅中,打上「內容不明「的標記,藏在神學院、圖書館中。
薩爾皮遺骸的第九次褻瀆發生在 1846 年,「...... 11 月 1 日『亡靈日』那天,威尼斯人蜂擁穿過通常緊閉的聖米歇爾大教堂大門,前往聖坎波爲朋友掃墓時,他們驚訝地發現保羅修士墓的所有痕跡都無影無蹤了。大理石板不見了,中庭的路面也恢復了原樣。…接下來當局開展嚴格調查,想找出這一暴行的始作俑者。…根據奧地利警方的記錄,調查結果指向聖米歇爾修道院的修道士,他們得到了威尼斯牧首的命令,而牧首又是按照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的指示。」
石板找到了,藏了起來,但沒有被毀壞,石棺還在原處,有堅固的金屬條捆綁。1846 年 11 月 19 日舉行了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安葬儀式;薩爾皮死於 1623 年。死人不會講故事,但屍體一定會。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十架路出版社英文網站:5 Myths about Galil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