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31年裡,我一直都在一間基督教大學教英語文學,這讓我感到很蒙福。我說這是一種「蒙福」,因爲我的職業不僅使我能夠充分利用我在世俗大學本科和研究生院九年的學習中所得到的知識和技能,而且還能對來自所有(或沒有)信仰背景的學生做福音見證和開展門訓。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有很多次不得不在學術上培訓和指導學生與在屬靈上引導和挑戰他們之間做出選擇。
幾個月前,我的學校從休斯頓浸信會大學(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改名爲休斯頓基督徒大學(Houston Christian University, HCU),這使得我們能夠擴大我們的使命和招生的範圍。幸運的是,在我和我的同事們一起經歷這一轉變的同時,一位慷慨的捐贈者給了我們一個獨特的機會,讓我們思考和禱告,在一所致力於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以基督爲主的大學裡做教師意味著什麼。
這位捐贈者提供了資金,以便在未來幾年內,所有教職員工都能少教一門課,以加入由一位資深教員帶領、每學期進行的小組。在這個小組中,我們將學習關於聖經和基督信仰的基本教義,同時討論基督徒生活的兩個關鍵領域:靈命塑造和福音宣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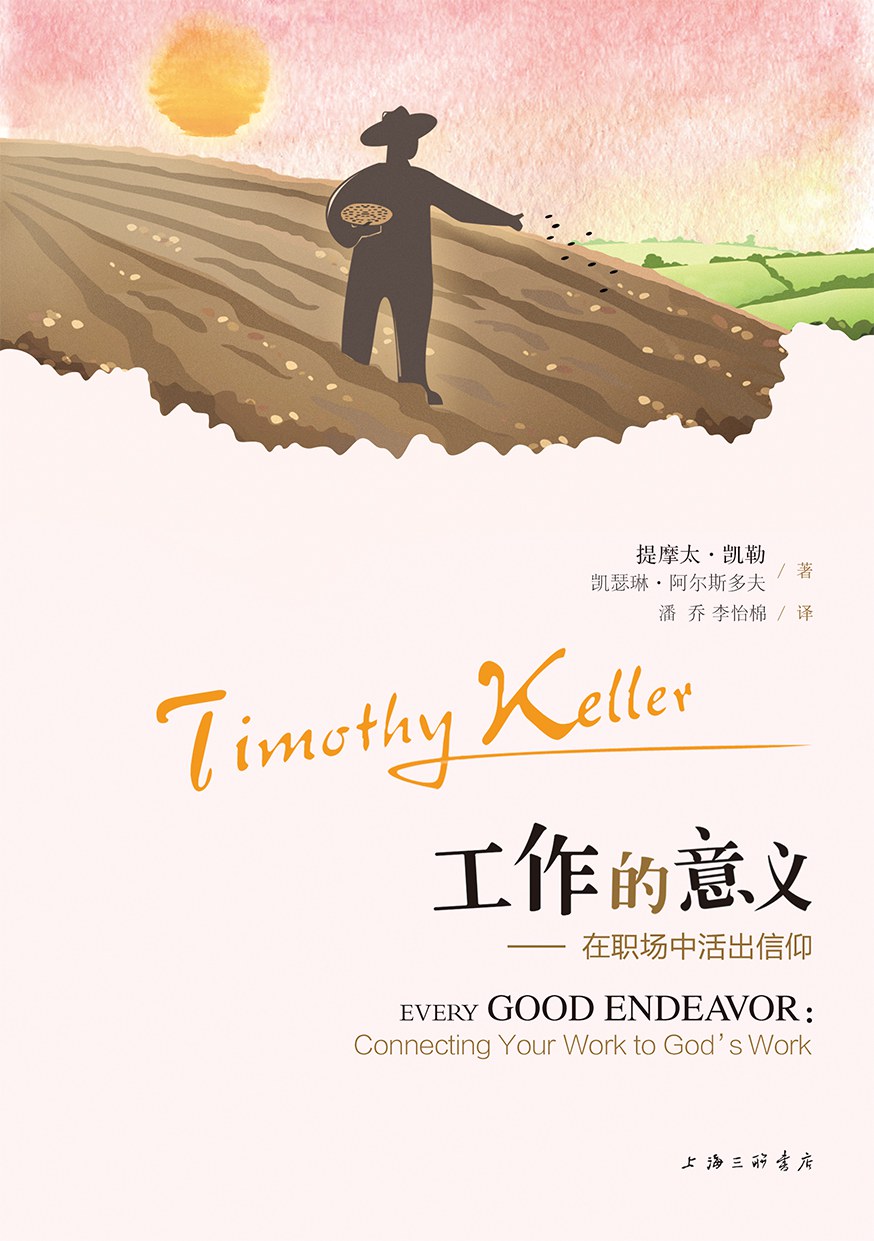 今天,很多人會交替使用「天召」(vocation)和「職業」(career)這兩個詞,但這兩個詞的詞源是完全不同的。後者指的是一條道路或路線,而前者指的是「召喚」(想想呼叫vocal這個詞吧)。爲了幫助我們思考我們所蒙呼召的深度和廣度,我所在的小組於2022年秋季已經深入學習了提摩太·凱勒的《工作的意義:在職場中活出信仰》(Every Good Endeavor: Connecting Your Work to God’s Work),以幫助我們將我們的工作與神的工作聯繫起來。
今天,很多人會交替使用「天召」(vocation)和「職業」(career)這兩個詞,但這兩個詞的詞源是完全不同的。後者指的是一條道路或路線,而前者指的是「召喚」(想想呼叫vocal這個詞吧)。爲了幫助我們思考我們所蒙呼召的深度和廣度,我所在的小組於2022年秋季已經深入學習了提摩太·凱勒的《工作的意義:在職場中活出信仰》(Every Good Endeavor: Connecting Your Work to God’s Work),以幫助我們將我們的工作與神的工作聯繫起來。
雖然這本書是十年前出版的,但凱勒的書並沒有失去與我們的相關性;事實上,它爲我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參考,讓我思考主呼召我從事的職業。我將與大家分享我在三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所學到的三件事,而學習凱勒的書幫助我釐清了很多想法。
在對我的博士論文進行最後潤色時,我開始向全美各地的大學發出簡歷,尋求任教的機會。我告訴主,我願意去祂呼召我去的任何地方,但作爲一個在郊區長大並在世俗學校上學的北方人,我很確定祂不會把我送到南方、大城市或基督教學校。神仔細聆聽了我的禱告,然後出於祂慈愛的護理,祂把我送到了美國第四大城市的一所南方基督教大學擔任教師。
我蒙召來到HCU當老師除了證明上帝有幽默感之外,還告訴我:神要我走出舒適區,神有工作要託付給我,但是神已經預備和裝備了我去完成這託付。在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讀本科時,我有感動去上一些關於印度的課程,儘管我以前從未見過來自印度的人。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快要畢業時,我在國際學生事工(ISI)服事,帶領一個韓國人團契和一個中國人團契的查經。但我沒有想到的是,神會派我到這個國家最多元的大學之一,教導來自亞洲(尤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學生。
凱勒認爲,「只有當另一方呼召你去做,而且你是爲了他的緣故而不是爲了你自己的緣故而去做的時候,某件事情才能成爲一種天職或天召。」(55頁直譯)這不是說你不喜歡或反感這項工作,恰恰相反,這讓工作變得更加充實,因爲你是蒙召去做這件事——不是把它當作一種證明自己或加添自身價值的手段,而是作爲對創造和救贖你的那位神的愛和信任。
正如凱勒解釋的那樣,馬丁·路德通過重拾聖經中因信得救的教義,打破了基督教事工和世俗工作之間的人爲障礙。「如果宗教工作完全不能爲我們贏得在神面前的更高地位,那麼我們就不應當視全職宗教工作優於其他形式的勞動」(63頁,直譯)。因此,路德使基督徒擺脫了對屬靈和智識工作的過高評價和對世俗、體力工作的輕看。
路德進一步說到,應當把工作看作是愛心的快樂流露,而不是證明我們自己的繁重努力(63-64頁直譯):
福音使我們擺脫了必須通過工作來證明自己和保證自己身份的無情壓力,因爲我們已經得著了來自福音的證明和保證。……既然我們在基督裡已經擁有其他人爲之努力的東西——救贖、自我價值、良心與和平——現在我們可以僅僅爲愛神和愛我們的鄰舍而工作。這是一種快樂的犧牲,一種提供自由的限制。
每種職業,包括教師,都有其限制,但這些限制既使我的工作更有意義,也有助於將我塑造成上帝創造我要成爲的那種改變者和塑造者。誠然,我的學生進入大學時的學習技能比30年前,甚至5年前要低得多;他們的焦慮也確實比以往要高。但這只是讓我有機會作爲一名指導者能更直接地幫助他們,希望看到他們成長和成熟,並幫助他們獲得必要的信心,使他們興盛。
在越來越多需要直接指導的學生中,我最欣賞的是與第一代學生——也就是家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之間的互動。與這些學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自傳統的中南美洲移民家庭)的密切互動迫使我審視和重新評估自己對工作性質和價值的看法,也讓我重新接觸到自己的文化根源——因爲我的祖父輩是1930年左右來到美國的四個希臘移民。
我在現代世俗學校和大學學習的這些年,使我對工作的看法變得根深蒂固,也就是崇尚自主和自我表達。但我所接觸的第一代學生則使我重新認識到,工作是爲自己的家庭、民族和文化服務的一種更傳統、更集體的努力。凱勒很好地描述了這兩種對生命、勞作和成功的定義之間的區別(134-35頁):
過去和現在的傳統文化對世界的理解包含了道德的絕對性,並且這種理解主要通過傳統和宗教獲得。智慧則透過父母、牧師和掌權者等權威人物從一代傳到另一代。這種文化教導他們的成員,如果他們承擔並忠於他們在社區中的職責和角色——作爲兒子和女兒,作爲父親和母親,以及作爲他們部落和國家的成員——他們的生活就有意義。
儘管凱勒繼續揭露了傳統文化可能陷入的一些特定的偶像,但他鼓勵他的讀者考慮,自從啓蒙運動取得勝利以來,西方文化與這些古老的價值觀之間有多大的差距(137-38頁):
現代社會推翻了宗教、部落和傳統等偶像,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經驗主義和個人自由作爲壓倒一切的終極價值。……現代社會不再認爲社會包含有約束力的道德真理規範,而所有的人都必須服從。相反,他們堅持認爲,沒有比選擇他或她想要的生活這一權利更高的標準。
像大多數大學教授一樣,我在很大程度上無意識地被普遍存在的理性、選擇和個人自由的世界觀所訓練,也在鼓勵我的學生利用他們所受的教育來重新定義自己和人生的目的。我清楚地記得與一位同事的談話,他主張教授需要推動他們的學生擺脫束縛性家庭關係,這些關係會阻礙他們在大學裡取得優異成績和找到有意義的工作。雖然我當時同意,但我的第一代學生幫助我醒悟到這種觀點的屬靈危險。
我慢慢意識到,上帝對我一生的呼召,不僅僅是教書,也是學習。現代工作觀念帶來了巨大的進步和創新,使婦女、少數民族和經濟上處於弱勢的群體能夠追求更多的職業道路。但他們這樣做是有代價的,我與第一代學生以及來自傳統家庭的印度、越南、尼日利亞、菲律賓、埃及和哥倫比亞學生一起工作,這使我了解了這種代價的本質。
我不再認爲我的任務是將傳統學生變成現代學生。相反,我努力幫助我的第一代學生,以及其他有強烈家庭和種族聯結的學生,在不犧牲他們的文化之根和他們使命感的情況下,在現代美國獲得成功。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我不得不重新思考的不僅僅是我對天召的認識,還有我的個人呼召是什麼大敘事(或元敘事)的一部分。凱勒解釋說,這個敘事「必須有一個關於應當如何生活的解釋,一個關於它如何失去平衡的解釋,以及一些關於如何使生活恢復正常的方案」(155頁)如果使人類失去平衡的罪魁禍首是無知,那就簡單了。因爲如果是這樣的話,像我這樣的教師就會成爲真正的英雄,因爲我們會擁有超級的力量,只需教育每個人就能帶來烏托邦。
但人的問題不是無知,而是對神的犯罪、悖逆和不順從。因此,教師的角色不是救世主和救贖者,而是指導者和導師。考慮到這一現實,凱勒就我們講述的敘事和我們接受的職業之間的聯繫提供了進一步的建議:「我們的世界觀將我們的工作置於一個歷史、一個事業、一個追求以及一組主角和對手的背景中,這樣做是爲了在高層次上確定我們工作的戰略。在日常層面上,我們的世界觀將塑造我們個人的互動和決定。」(158頁)
大學有著悠久的歷史,根植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學院(Lyceum)和中世紀的天主教大學。雖然它在基督教之前和基督教時期表現有所不同,但這兩個階段都認爲(1)教育的原因是使心靈從這個世界的妄想和誘惑中解放出來,(2)教育的追求是使學生能夠感知到真、善、美,其對立面是無知,但這是一種故意的無知,在頑固地拒絕看、拒絕理解、拒絕改變方面與罪緊密相連。
我的使命不是要治癒或救贖無知,而是要突破無知,喚醒學生,讓他們擺脫困惑、懶惰和驕傲的桎梏,釋放出敬畏、謙卑和感激之情。當我教學時,我的目標是吸引他們進入我們正在閱讀的文本,進入自摩西和荷馬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偉大對話。當我教學時,我的目標是激發他們的自信心,讓他們相信他們有能力,有權利加入這場對話。
我拒絕後基督教大學的世界觀,它把知識等同於懷疑,把智慧等同於看穿過去的信仰和傳統(他們會說這都是迷信和體制)的批判能力。相反,我盡我所能培養這樣一種認知:蘇格拉底認爲奇蹟從知識開始,而教會認爲智慧從敬畏耶和華開始。
柏拉圖和中世紀的大學是精英主義的,服務的是少數富人和天賦異稟的人,但我在HCU的角色是將教育的祝福擴大到過去沒有機會上大學的學生,他們是我蒙召去服事的新鄰舍。
耶穌的第一代追隨者大部分是窮人,沒有受過教育、生活在強大羅馬帝國的邊緣。另一種第一代現在正坐在我的教室裡,我爲能夠門訓他們而感到蒙福。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Tim Keller Made Me a Better Teac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