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議的那樣,我們要幫助我們的讀者「讓這幾個世紀以來乾淨的海風吹過我們的心」(出自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譯註)。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只有通過閱讀經典」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接下來要審視一些可能被遺忘、但是依然和現今的教會相關,並且能幫助今日基督徒的經典著作。
對於今天很多人來說,1960年代是古老的歷史,對於當今這個短視的時代而言,歷史和過去都沒有太大意義。但是過去永遠是現在的關鍵。如果不了解60年代,就不能了解美國和西方當前的危機。
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西方文明的領袖——美利堅式的共和——內部存在著自內戰以來最深刻的分歧。爲什麼會這樣?這僅僅是「沿海地區」(紐約和加利福尼亞州)與「心臟地帶」(中西部和南部)之間的衝突,還是「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川普總統所謂「被遺忘的人」)與「全球主義者」(像喬治·索羅斯這樣的西方精英)之間的衝突?這種深刻且痛苦的兩極分化背後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深層的分歧幾乎被完全忽略了,其實這一過程是經六零年代加速而成的。美國目前分歧的最終根源在於,在那些根據美國大革命及其傳承來思考自由的人與那些根據法國大革命及傳承來考慮自由的人之間存在著對自由的不同概念。
讓我們想一想諸如「進步主義」,「後現代主義」,「政治正確」,「身份與部落政治」或「性革命」之類的思潮吧,想一想社會主義最近的聲望飆升,還有民主黨和許多媒體向左漂移,我們很快就會清楚地發現,這些思想與1776年美國革命以及美國的自由觀幾乎沒有關係。這些思想源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法國啓蒙運動及其後來的接棒者直接或間接提出的思想,這些人包括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尼采,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因此,1960年代的意義及其對「革命信仰」的表達源自法國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激進的六十年代」,及其帶來的「青年地震」(克里斯托弗·布克),「反文化的形成」(西奧多·羅斯扎克),以及「美國的綠化」(查爾斯·賴希),其實是激進思想闖入了美國主流思想和生活的十年。更重要的是,六零年代是播下許多當今最激進思想種子的年代,只是最近才以其最具破壞性的形式開花,例如「變性主義者」極端主義和「安提法」的暴力運動。
出版於1973年,由本人所著的《死亡的灰塵:六十年代的反文化及其如何改變美國》(The Dust of Death: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 Forever)是一次從記者角度所寫下的嘗試,試圖公正記錄1968年我第一次訪問美國時所目睹的一切。我對第一次造訪美國會看到什麼和經歷什麼毫無預備,那年後來被描述爲美國的「偉大紀元」(annus calamitous)。《時代》雜誌的蘭斯·莫羅(Lance Morrow)在1968年寫道:「就像刀刃一樣,這一年切分了未來和過去。」 歷史學家悉尼·奧爾斯特倫(Sydney Ahlstrom)將這十年描述爲「美國歷史上的決定性轉折點」。喬治·威爾(George Will)將1968年稱爲「也許是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並將60年代描述爲「美國作爲一個國家生命中最危險的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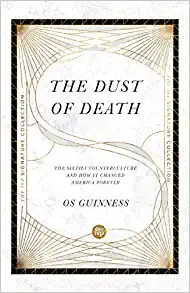 那一年,美萊村大屠殺的恐怖被公諸於世、4月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殺、7月羅伯特·肯尼迪參議員被殺;抗議發生後,有一百多個美國城市在燃燒;反越戰運動風起雲湧。五月,以學生爲首的激進抗議活動使法國總統戴高樂的政府屈服,許多人希望總統林登·約翰遜的政府也能這樣。
那一年,美萊村大屠殺的恐怖被公諸於世、4月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殺、7月羅伯特·肯尼迪參議員被殺;抗議發生後,有一百多個美國城市在燃燒;反越戰運動風起雲湧。五月,以學生爲首的激進抗議活動使法國總統戴高樂的政府屈服,許多人希望總統林登·約翰遜的政府也能這樣。
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許多標誌性事件還沒來到,我說的標誌性事件包括了1969年8月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興高采烈、1969年12月滾石樂隊阿爾塔蒙特音樂會的暴力事件、1970年5月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以及耶穌運動的驚人爆發等等。 但是1968年發生的事情就已經足夠讓我得出結論了。反文化衝擊正在形成,但無論是激進分子、他們的啦啦隊長,他們急切的反對者以及西奧多·羅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和查爾斯·賴希(Charles Reich)等評論員都錯了。革命的夢想和成功反文化的希望按著他們的努力方式注定了不會成功。保守派在1980年代宣告自己「在60年代的墳墓上跳舞」同樣是錯誤的。1968年已經很明顯地證明了六零年代思想是激進的,是強大的,但存在致命的缺陷。 馬賽·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死亡之塵」開始爲60年代的夢想和激情埋下伏筆,預示了它的終結。
與1971年相比,現在我能清楚地看到更多東西,有些事情我會以不同的方式去寫。文化分析從來都不是奧運會。它不僅涉及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而且是就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而寫的,僞裝這點也沒有任何益處。《死亡的塵埃》是基於六零年代的角度對六零年代進行的分析。接下來的每一年都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寫出60年代的故事。但這樣推論下去沒有什麼好處,最好先承認這一分析所處的時間和地點,然後詢問其論點和結論是否仍然成立。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爲這本書的核心論點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這與一些現在看來不過是六零年代的烏托邦式夢想的書籍截然不同。。
當然,在某些地方,我今天再寫的話會有所不同。首先,儘管在六零年代對這些詞就已經有所批判,但「人」、「現代人」和「西方人」等術語在今天仍然得到廣泛使用。此外,自那以後我更多地使用「基督信仰」而不再是「基督教」這個詞,我發現從「基督」到「基督徒」再到「基督教」的發展,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都是朝著去位格性和抽象概念的方向發展。
其次,我過分依賴思想史作爲工具。今天,我認爲知識社會學的互補方法同樣重要。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從思想家到他們對日常世界的影響(思想在雨水中如何被沖刷下來);而後者則是自下而上,從日常的世界到它對我們所有人(包括思想家們)思想和生活的影響。對於深受電視和藥丸,以及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影響的一代人,對知識社會學的忽視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第三,今天我在使用「第三條道路」這一概念時會更加謹慎。可以肯定的是,早期基督教運動作爲不受歡迎的兩個極端之間「第三種人」的先例令人鼓舞,並且仍然重要。但是「第三條道路」和中間策略的概念(例如克林頓總統著名的「三角策略」)卻與原則無關,而更多地是在做無原則的差異分割。更糟糕的是,我並不是說耶穌的追隨者應該離開所有其他團體和政黨、只爲明顯和獨特的基督教運動而努力,正如批評家所指出的那樣,這種誤解缺乏現實主義,導致被人們合理地駁斥爲「直升機思維」。在尋求明確,純正的基督徒立場時,許多基督徒仍然徘徊在空中,無法在公共政策問題上做出必要的選擇。話雖如此,「第三條道路」的概念及其在這個充滿偶像崇拜,兩極分化和極端主義的世界中仍然是一個很實際也很有洞見的想法。
還有第四個也是至關重要的領域,事後證明這一領域非常重要,關鍵在於理解「體制長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自1789年以來,「遠征」("the grand march")這個詞就常被用來描述「革命信仰」的向前發展以及其博愛、平等和團結的夢想。但「長征」並非如此,把這個詞引入西方文化的是西德紅色旅(Red Brigades)領導人魯迪·杜特奇克(Rudi Dutschke),他用這個詞宣揚他在反文化失敗後敦促激進左翼採取的策略,這個詞是指對毛澤東1934年在中國進行的長征。在那次革命中,毛澤東逃脫了包圍他的國民黨軍隊,向北行進了6000英里,然後重新集結,後來席捲了整個中國,並在1949年贏得了共產黨的最後勝利。
1920年代的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坐在墨索里尼(Mussolini)的監獄裡,將馬克思失敗的革命視野重新定義爲所謂的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在他的《監獄筆記本》中,他認爲革命應該是緩慢而漸進的。它的目標必須是通過滲透社會中的「守門人」和「切入點」,在「統治階級」中取得統治地位(「文化霸權」),首先是「消滅」統治階級的前任領導人,然後慢慢用新的革命思想和敘事方式取代他們。如果革命者以這種方式獲得「人類意識的掌握」,那麼他們就不需要集中營和大規模屠殺。因此,用杜特克(Dutschke)的話說,「革命不是短時間的行動,好像事情發生一次,然後一切都會不同。革命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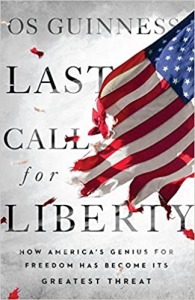 五十年後,很顯然,對體制的長征已經相當成功。學術界,媒體和好萊塢都反映了1789年繼承人的思想,而不是1776年的理想。美國已被迷住了。這個共和國正在將革命從美國式轉向法國式。我曾嘗試在我2018年出版的《最後的自由呼籲》(Last Call for Liberty: How America’s Genius for Freedom Has Become Its Greatest Threat)中解決當前的困境:這裡的重點是,儘管當時還不很明顯,但六零年代播下了產生今天苦瓜的有毒種子。這些想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六零年代之前,但是到了六零年代,它們才變得危險起來。
五十年後,很顯然,對體制的長征已經相當成功。學術界,媒體和好萊塢都反映了1789年繼承人的思想,而不是1776年的理想。美國已被迷住了。這個共和國正在將革命從美國式轉向法國式。我曾嘗試在我2018年出版的《最後的自由呼籲》(Last Call for Liberty: How America’s Genius for Freedom Has Become Its Greatest Threat)中解決當前的困境:這裡的重點是,儘管當時還不很明顯,但六零年代播下了產生今天苦瓜的有毒種子。這些想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六零年代之前,但是到了六零年代,它們才變得危險起來。
總而言之,1960年代是一個迷人的時代:色彩繽紛,熱情洋溢,喧鬧,憤怒,陶醉和動搖不已。但是它們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政治、文化或歷史。那個時期塑造了一代人的生活、信念、希望、經驗和視野,這一代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是學生,但現在已成爲國家的領導人和守門員。
無論如何,我們都是60年代的孩子,我們需要評估那個決定性十年給我們留下的最好和最壞的遺產。
譯:Angel Lau;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e're All Children of the Six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