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對千禧一代(Millennials,一般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人,是源自美國文化對一個特定世代所習慣稱呼的名稱——譯註)的分析都喜歡關注他們的獨特之處。但要記住的一個關鍵點是,在許多方面,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只是顯得更強烈。換句話說,他們也拒絕接受上幾代人身上的種種大趨向,但依著歷史發展和邏輯發展的軌跡,他們在這拒絕的程度上走得更遠一些。和其他人一樣,他們也生活在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稱之爲「新星效應(Nova Effect)」這樣的認識論和道德環境中。(《世俗時代》,英文版第299-321頁)
正如泰勒所解釋的那樣,500多年前,大家都默認信仰上帝。如果有一個人自稱相信無神論能使人心得滿足、使人更像人,那簡直就像今天有人說自己相信獨角獸一樣。隨著「現代性」和啓蒙運動的到來,「排他性人文主義(exclusive humanism)」(也就是人本主義的無神論)作爲一種可行的、可替代基督信仰的另一選擇隨之而起。然後隨之而來的是懷疑論者、有神論者、基督徒和浪漫主義者之間的論戰爆發,引發的連鎖反應導致了可供選擇的「靈性信仰」多樣性不斷增加。新星效應已經成爲了「一種在靈性層面上馳騁的多元主義」(英文版第300頁)。
從實際應用上看,這種新星效應意味著幾件事。首先,我們都被幾十種選擇交叉施壓,讓每個人的信仰都「變得脆弱」和不穩定。如果你是一個有神論者,在你看著最新的網飛(Netflix)視頻平台上的關於宇宙的紀錄片時,你仍然會感受到內在的另一種聲音在吸引你,這聲音誘導你去相信一個無神的宇宙在智識和存在層面上都是可行的、可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懷疑論者,神的超然存在感會對你發出召喚。每當你在當地的荒野小徑上遠足,上帝都會用滲過樹叢的縷縷陽光使關於祂的念頭不斷縈繞在你心頭。
換句話說,我們都認識一些有智識又理性的人,他們的生活和我們差不多,但信仰的東西卻截然不同。你的錫克教鄰居,你的佛教徒健身夥伴,還有你的無神論者同事,他們在同一家小眾食品店買菜,追看漫威系列超級英雄電影,並且愛各自的家庭。但他們都不會在週日去你的教會。這個世界已經不再有一個單一的、明顯和公認的世界觀,信仰已經不再是一個只有開和關兩種狀態的開關,而是一系列你可以設置不同程度的撥盤(後世俗、人文主義、浪漫主義、自由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等等)。
那麼,我們如今該如何設置這個撥盤呢?在這個追求「真實」的時代(Age of Authenticity,想想1960年代後的生活),我們的動力是確保——無論影響我們決定的因素都有哪些——我們「對自己真實」。這就是「表現型個人主義」("expressive individualism")在信仰塑造中的作用。 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仍然會選擇傳統的信仰,比如天主教、福音派新教,或者其他主要的世界宗教之一。但是沒有人再簡單地繼承他人給予的「信仰包袱」了,我們要自己選擇(甚至構建)一個「信仰包袱」,這往往是我們自我實現項目的一部分。
由此產生的混合體各不相同。一個人的信仰可能是這裡有一點基督教、那裡有一些治療心理學,還有一丁點追求社會正義的進步主義作爲補充。另一個人可能選擇佛教作爲基礎,加上一些西方的理性主義,還有對健身運動的承諾。之所以會有這種「必要的異端」("heretical imperative")是因爲這樣一種意識:屬靈的元素有助於尋找我們獨特的定位和自我。藉此,美國已經成爲一個生產異端的大國,或者說,混合主義大國。
談到千禧一代的與眾不同之處,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他們彼此之間也有差異。不過,千禧一代區別於其他世代的最重要標誌之一是他們成長於互聯網時代。「谷歌」(Googling)作爲一個動詞,在10年前才被《韋氏大詞典》收錄,這意味著這個詞的使用時間更久。對於千禧一代來說,用這個詞的時間相當於我們一生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時間。
如果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宗教的超新星爆發時期,互聯網更是進一步放大了這個問題。瀏覽你的臉書(Facebook)新聞源,你會不斷地被政治、種族、性別和精神方面的不同觀點所轟炸。 不要緊,如果你很好奇,實際上你也是在尋找不同的選擇。
這種效應會帶來幾件事。首先,基督教已經失去了(大量的)主場優勢。它現在是市場上眾多競爭者中的一個,其中一些競爭者的長處是就現代西方的性和經濟倫理而言可塑性明顯增強。儘管基督教仍然聲稱在美國千禧一代當中的市場份額最高,但這一代人當中認爲自己不屬任何宗教的比例高於其他任何一代人(34%的不歸屬任何宗教,46%的基督徒)。這並不是說他們是無神論者,但他們並不那麼容易宣稱自己有特定的宗教傳統。
其次,宗教中權威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現代性一直有一種內在的反權威、反體制、反教廷的風氣。但是,互聯網使個人主義和實踐的認識論更加徹底。對現代人來說,社群不再扮演著傳統的宗教真理保護者、權威來源的角色。
例如,宗教神職人員的價值和地位比過去少了很多。千禧一代覺得不需要等待牧師告訴他們對一節經文的最佳解讀。當你可以自己在谷歌上搜索任何東西的時候,神學院的學位又算得了什麼呢?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不喜歡你的牧師說的話,你可以在講道的過程中用你的手機查找其他的選擇——你可能比他更懂得如何使用手機。事實上,千禧一代對技術的更大適應性也有助於將權威從年齡轉移到年輕人身上——孩子們在教他們的祖父母使用他們作爲第二自然肢體的導航設備。年長的人更需要年輕的人,而年輕的人則不那麼認爲他們需要年長的人。而且現在的年輕人也不認爲在20多歲時出版回憶錄有任何諷刺意味。
與前幾代人不同,千禧一代當中成熟的榜樣令他們更多地與長輩對立。泰勒在他的書中所提到的最近護教學張力解釋了皈依無神論或排他性人文主義是如何被特定的道德敘事所驅使的。這些離開基督教信仰的人並不是簡單地面對 「科學」,然後按照一個三段論得出沒有神的邏輯結論,並因此決定上帝沒什麼價值。相反,背道者更多地是看到和跟隨了因爲懷疑而離開信仰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中,懷疑是一個英雄個體不計代價地步入知識的成年與成熟的方向。從他們早先幼稚的信仰中走向專一的人文主義,需要 「諸如脫離的理性,放棄安慰式幻想的勇氣,依靠自己的理性對抗權威」(《世俗時代》,英文版566頁)的美德。雖然不容易,但懷疑是勇敢的、堅強的、大膽的。
那麼,考慮一下最近的「後福音派」回憶錄/見證的出版,這些著作往往以年輕作者的屬靈旅程爲中心,對千禧一代極有吸引力。雖然種類繁多,但這些回憶錄往往有一些共同點:這些以「自我發現」爲內容的第一人稱敘事,並不像過去典型的信仰英雄故事那樣。相反,它們往往重視懷疑和不確定性,而這與當下媒體文化中提供的更廣泛的信仰破碎的文化敘事是吻合的。
具體的掙扎和疑惑因題材不同而不同。有些人在信心、反智主義和科學等問題上掙扎,以尋找比對這些艱難問題常見膚淺的回應更好的答案。另一些人則是爲了逃離基要主義和福音派社區的律法主義、操控和濫用權柄。還有更多的人專注於重新考慮教會對性和/或同性婚姻立場的挑戰。
但不管是什麼問題,面對這些交叉壓力和脆弱的條件,存在和認知上的不協調,他們以前的信仰已經變得不堪一擊。主角們進入了信仰的新階段——也許是破碎的、傷痕累累的,有點不確定,但更真實、更冒險,並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信仰。藉著在疑惑的火焰中接受洗禮,他們拋開了淺薄的、治療性的青年團契(和他們的父母)簡單、天真的信仰。他們已經敢於去了解。
我的觀點並不是要批判這些故事——有些故事提出了有效的批判,我們應當了解它們——而只是想指出它們與新星效應下的信仰倫理的聯繫。以英雄的懷疑爲成熟的倫理至少解釋了它們的一些吸引力。一些回憶錄作家很快就承認他們提供了一個關於世界的 「觀點」,並且謙虛地知道這不是唯一可信的觀點;另一些人則通過簡單地調整信念以適應不同的壓力來緩解緊張局勢(即使這涉及到重寫兩千年來所接受的基督教教義)。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認識到需要喘息的空間,因爲普通信徒感到迷失方向、猶豫不決、充滿疑問和疲憊不堪。
因此,這些敘事產生了另一種形式的屬靈和道德權威,這權威就是「真實」。在這個真實性時代,苦難、掙扎和懷疑的見證爲你贏得了被傾聽的權利。不僅僅是被傾聽,甚至是作爲一個榜樣被追隨——不是因爲無懈可擊的真理,而是一個有同情心的、真實的、同爲懷疑者的人,這樣一個人不會迅速地對我們的弱點作出判斷,他向我們揭示了我們在這些弱點中可以找到的力量。
考慮到這些因素,那麼,我們該如何服侍超新星中的年輕一代呢?
第一,摒棄絕望和懷舊
首先,我們需要拒絕絕望的誘惑,或者對一些神話般的、失去的信仰黃金時代進行悲觀的、令人崩潰的懷念。正如泰勒所指出的,早先的年代也許沒有遭受到多元主義、脆弱化和交叉壓力的掙扎。但在基督教世界裡肯定存在著更大的誘惑,即屬靈的專制、虛僞和社會順應的淺薄 「信仰」。
事實上,克爾凱郭爾(祈克果)十幾本書(其中一半用的是筆名),試圖向基督教世界解釋新約基督教不是簡單的「抽屜裡躺著一張洗禮證書,當一個人要入學或要舉行婚禮時,就把它拿出來」的那種信仰(《終結中的非科學後記》,卷一,英文版367頁)。
他受夠了,也不聽話,在生命的最後,他發起了他那轟轟烈烈的、全力以赴的 「對基督教世界的攻擊」("attack on Christendom"),這應該讓我們大家在對昔日的基督教文化事工過於懷念之前,先暫停一下。如果我們的語境逼迫我們向千禧年的聽眾傳講真誠的信仰,爲什麼不把他的警告當作是來自主的提醒呢?
第二,講道中帶著護教
我們還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這個時代給我們帶來的優勢。在真實性時代,唯物主義和排他性人文主義並不自動佔上風。在早先的幾十年裡,基督教可能被認爲是西方默認的宗教,而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作爲更明顯的智力選擇,在精英圈裡佔據了優勢。但由於超新星並沒有直接轉化爲無神論,因此爲「屬靈」對話創造了更多的知識喘息空間。基督徒仍然有機會將福音作爲一種美麗的選擇,以取代主宰我們景觀的逼仄的身外之物意識形態。
我們已經到了每個人都要在講道中護教的地步,即使你的會眾大多不是千禧一代。要說明的是,我不認爲這樣的講道是簡單地在每一次講道中加入復活、或神的存在等論據(雖然有些論據可能會有幫助)。相反,我們需要定期從我們交叉壓力文化的思維方式裡面積極地回答對福音的反對意見,作爲我們經文講解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向這一代人展示福音的一致性、連貫性和可愛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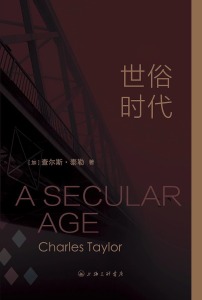 但是,僅僅爲福音護教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向這一代人展示福音的一致性、連貫性和喜樂。呈現出它如何審問我們聽眾當中主流的、不受質疑的關於意義、金錢、性別、權力、政治、性別等等的敘述,並且實際上比其他任何觀點都更能理解這個世界。
但是,僅僅爲福音護教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向這一代人展示福音的一致性、連貫性和喜樂。呈現出它如何審問我們聽眾當中主流的、不受質疑的關於意義、金錢、性別、權力、政治、性別等等的敘述,並且實際上比其他任何觀點都更能理解這個世界。
泰勒的《世俗時代》在這裡是一個典範,因爲整部作品都在顛覆世俗主義者告訴自己的關於他們如何通過不信來實現的故事。他並不是「證明他們都是錯的」,而是讓競爭環境變得更公平,在他們的敘事中戳出漏洞。如果你好奇這樣做意味著什麼,可以讀一讀提摩太·凱勒。
當我們以護教的方式講道時,至少能收穫這幾個果子。首先,我們清楚地表明,福音聲稱自己是真理。這個焦點有助於防止基督教被採納爲另一種自我表達的靈性,選擇它僅僅是因爲「它對我有效」。其次,它開始解決許多千禧一代的實際問題和掙扎。即使我們不能回答每一個問題,我們也可以開始向他們展示,在這些問題上,除了他們在主日學接受的半記半背的課程之外,還有一個強大的、知識性的基督教思考傳統。正確的護教式講道承認信仰上的壓力,即使它努力從這種壓力環境中呈現基督教。
第三,爲多馬留出空間
在這裡我想到了多馬的故事,他是我們當中典型的懷疑者。當他聽到其他門徒的見證時,他不相信(約翰福音20:25)。他沒有看到復活的基督,所以在沒有看到之前,他拒絕相信。對本文的目的來說,多馬身上有幾點是突出的。
在後來的那一個星期裡,多馬一直和其他門徒們在一起——在充滿復活希望的門徒中間,多馬是一個不信的人(約翰福音20:26)。好像門徒們知道對多馬來說他們所教導的事情是多麼荒唐可笑,所以他們耐心地給他留出空間,直到主來訪。
同樣,有興趣向千禧一代傳福音的教會也需要熟練掌握那種耐心,慷慨地給提問者、受到交叉壓力的不信者留出空間。教會不應該是一個容易做出過度反應的地方,也不應該是一個快速提供談話停止的陳詞濫調的地方(這些陳詞濫調會在無意中壓制人提問的願望)。必須歡迎提問和對話。
這種做法其實是在呼喚一個更健全的教會論和共同體,而不是一個單薄的團體。有著強大的成員制度和教會紀律的教會,其實有著必要的穩定性,可以在不破壞共同體穩定性或破壞共同信仰告白的前提下接納某個懷疑者一直在他們中間。
爲多馬騰出空間,也需要一定的謙卑信心,相信主最終會證實我們的信仰。對福音真理的非防禦性確信吸引了許多年輕的千禧一代。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經歷信仰危機,才能獲得必要的真實性分值來服事千禧一代。雖然我們「無法想像任何不帶有疑惑的確定性」,但我們不應該因爲某人的疑惑而承認他「特別真實、深刻、精細、優雅」。事實上,我們可以利用「真實性時代」的優勢,對真實的信仰需要危機的觀念進行反擊。爲多馬騰出空間,不應該要求我們變得和他一樣。
比起門徒們,耶穌自己就是我們與多馬打交道的典範。他來到多馬面前,慷慨地接納他,對他的問題不擔心,不驚擾。祂以自己的方式與多馬見面,以邀請他信靠自己——「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賽42:3)。
但最終,教會必須相信耶穌對多馬說的話:「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20:29)。那些憑著信心而不是憑著眼見行走的人是有福的。耶穌爲他們禱告,天父也聽了他的禱告(約翰福音17:20)。這應許是給我們的,也給我們爲福音的緣故而尋求服事的那些受到交叉壓力的千禧一代。基督已經爲他們上了十字架,他不會失去天父所賜給他的任何一個人——即使在世俗時代也不會。
譯:安卓;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Ministering to Millennials in a Secular 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