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本文改編自發表於福音聯盟學術期刊Themelios 45.2(2020年8月號)上的同名文章。
當我第一次戴著面罩和塑料手套去我們當地的雜貨店購物時,我被所看到的現實震撼到了。現實變得不太「正常」。2020年1月,世界首次了解到中國發生了一種名爲「新型冠狀病毒」的病毒流行並且感染了數千人。但到了3月,這一遙遠的疫情已經成爲世界性的流行病,感染了數百萬人、導致幾十萬人死亡,還造成了全球經濟的劇烈動盪,並從根本上打亂了大多數社會的正常運轉。到了今年復活節主日,大量教會停止了實體聚會,從學前教育到研究生課程的各級學校都被迫採用了在線和遠程學習方式,並爲畢業生舉行「虛擬」畢業典禮。許多大學和神學院也因招生人數下降、預算嚴重不足、前途不明而取消了一些教師崗位和學位課程。即使「居家隔離令」解除,企業和教會得以開始重新開放,《大西洋》(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也給出了清醒的評估:「我們已經無法回到『正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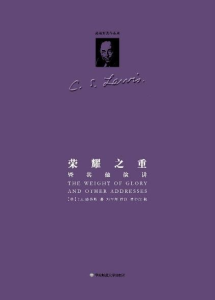 C. S. 路易斯80年前的一次講演爲這個不正常的時代提供了及時的洞見。當時牛津大學聖瑪麗教堂的牧師T. R. 米爾福德(T. R. Milford)求助於路易斯——畢竟後者是經歷過世界大戰的老兵,同時也是馬格達倫學院(Magdalen College)著名的基督徒講師——來回應牛津大學本科生在二戰初期的擔憂。於是,在1939年10月22日,路易斯向一大群牛津大學的師生發表演講,題目是「沒有別神:戰時文化」。後來這篇演說以小冊子的形式得著出版,小冊子題目是「處在危險之中的基督徒」,後來又以「戰時求學」爲題出現在路易斯的演講集《榮耀之重》裡。
C. S. 路易斯80年前的一次講演爲這個不正常的時代提供了及時的洞見。當時牛津大學聖瑪麗教堂的牧師T. R. 米爾福德(T. R. Milford)求助於路易斯——畢竟後者是經歷過世界大戰的老兵,同時也是馬格達倫學院(Magdalen College)著名的基督徒講師——來回應牛津大學本科生在二戰初期的擔憂。於是,在1939年10月22日,路易斯向一大群牛津大學的師生發表演講,題目是「沒有別神:戰時文化」。後來這篇演說以小冊子的形式得著出版,小冊子題目是「處在危險之中的基督徒」,後來又以「戰時求學」爲題出現在路易斯的演講集《榮耀之重》裡。
在這次演講中,路易斯提醒我們:「生活從來就沒有正常過。」他解釋了我們爲什麼以及應當如何爲了上帝的榮耀而追求認真的學習——無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他還強調了三個分散或阻礙學習的尖銳挑戰。本文試圖從路易斯的戰時講話中得著智慧,以告知和鼓勵牧師、神學生和其他在使徒們所說「現今的苦難」(林前7:26)中勞苦的讀者。
爲什麼一個正常人會在世界大戰或疫情大流行期間認真研究神學、人文學科或藝術?
鑑於就業市場的不確定性,這種學術追求似乎在資源和時間投資上來看是不明智的。有些專家甚至會宣稱,當數百萬人的生命岌岌可危時,埋頭於書本是不負責任的社會行爲。我們可能會認爲,在這種時候從事耐心、謹慎的學術研究類似於「琴照彈,休管羅馬大火」(英文版47頁,下同)。路易斯針對這類由於二戰的不確定性和緊迫性而對傳統大學研究提出的反對意見,認爲我們必須努力「以正確視角看待當前這場災難」(49頁)。一場戰爭(或者說一場疫情)並沒有真正創造出一個「新的局面」;相反,它迫使我們認識到「人類永久的處境」,即人們一直以來都「生活在懸崖邊上」(49頁)。「正常的生活」是一個神話:如果人們總是等候最佳條件出現,然後才去尋找關於真、善、美的知識,那麼他們將永遠不會開始。路易斯提醒我們,過去幾代人都有著他們的危機和挑戰,但人類還是選擇了追求知識和發展文化。在危機中,我們不可能中止我們的「理智及審美活動」(52頁)。即便在戰爭時期,我們也會繼續閱讀——問題是我們讀的是那些挑戰我們深思熟慮的好書,還是把時間花在淺薄平庸的分心上。
路易斯認爲,我們不應該把我們的活動進行「天性」或是「屬靈」的區分,因爲「每一種責任都是一種宗教呼召」(53-55頁)。無論某人是作曲家還是清潔工,是古典主義者還是木匠,當他們謙卑地將其「獻給主」時,他們的天性工作就變成了屬靈工作(55-56頁)。因此,即使在戰爭時期,對知識和美感的智力追求也可以而且確實會榮耀上帝。不過路易斯警告說,如果我們「不是爲發揮我們的天賦而心喜,而是爲此天賦屬於我們而心喜,甚至爲天賦給我們帶來的聲名而心喜」,那就是把學術上的成功變成了偶像。
在現代社會中,哪些職業是「必不可少」的?在疫情期間,大多數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暫時關閉了社會的許多部門,而只允許「必不可少」職業上的人繼續工作。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神學家的工作(例如)似乎是多餘的,而急診醫生和疫苗研究人員的工作在一個遭受致命疾病打擊的社會中被認爲是至關重要的。然而,如果我們考慮到人類社會的長期繁榮,這樣的評估其實是短視的。
哲學關注的是對智慧的追求。學習哲學的學生要學會提出合理的論點,深入思考什麼是真、善、美,並考慮我們應該如何在複雜的世界中生活。一個不重視真理、邏輯、美學、道德的社會,確實是一個糟糕的「勇敢新世界!」 路易斯呼籲基督教學者爲教會服務,要更加努力,更加深入地思考,以促進 「好的哲學」,提供真正的答案和合理的護教,以對抗這個時代的哲學潮流和時尚(58頁)。
同樣,我們也需要研究過去,以正確評價現在的挑戰和關注。正如傳道者提醒我們的那樣:「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1:9)「史無前例」這樣的字眼常常被用來形容新冠病毒大流行,然而我們這一代其實並不是第一代面臨致命疾病威脅的人。好的歷史學習可以讓我們「相對平衡地看待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時代」,從而更好地理解我們的世界和我們在其中的位置。通過分析過去的時代和民族,路易斯建議學生們認真學習歷史並建立起知識分子的抗體,「對本時代的書報與廣播中噴湧而出的胡言亂語保持免疫。」(59頁)
路易斯在《戰時求學》中沒有直接論述嚴肅的神學研究有怎樣的性質和必要性,但在其他地方,他的理由是,「任何一個想思考上帝的人,都希望有關於上帝的最清晰、最準確的觀念,這是一直會有的。」他堅持認爲神學是實用的,特別是在戰爭時期,因爲每個人都有自己關於上帝的想法(其中許多是錯誤的),並且容易受到各種神學「新知」的影響,對於這些「新知」,他說:「真正的神學家在幾個世紀以來都努力了解過,但最後都拒絕了這些錯謬。」新冠疫情擾亂了全球經濟,奪走了數十萬人的生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多數人的「正常」生活,但同時也迫使許多人對自己的死亡和終極問題進行掙扎。路易斯則認爲:「戰爭使得死亡對我們變得真實……我們再也不會看錯,我們一直居於其中並與之虛與委蛇的宇宙,是何種宇宙。」(62-63頁)將路易斯的話應用到我們當前的危機中可以幫助我們意識到,嚴肅的聖經和神學研究,在謙卑地服務於基督和祂教會的過程中闡釋「歷史性信仰的基石」,這是一個迫切的需要,也是一個機會。戰爭和疫情能夠提醒人們,在我們的世界中,有些東西是深深的錯誤。基督教神學通過揭示武裝衝突和流氓病毒是宇宙中最深層問題的表面症狀來告知人們這一根本事實:人類反抗造物主上帝,而造物主上帝將根據每個人的行爲來審判他們。因此,真正解決我們弊病的辦法不是在白宮或世界衛生組織,而是在髑髏地,在那裡,上帝的兒子爲罪人受苦和死亡,然後通過征服墳墓解除了死亡的武裝。
查閱圖書館檔案就會發現,確實有許多學生在牛津大學和其他大學開展「戰時學習」。著名的研究早期教會的學者弗倫德(W. H. C. Frend)於1940年在牛津大學完成了關於北非基督教的博士論文,喬治·凱爾德(George B. Caird)在1944年完成了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撰寫了關於新約榮耀概念的論文,並得以繼續擔任該大學聖經釋經學教授。在這些例子之外,我們還可以加上戰爭時期牛津大學關於法蘭西斯·培根對聖經的使用(1940年)、聖經後時期希伯來語法(1943年)、布克爾與英國宗教改革(1943年)、英國清教徒的崇拜(1944年)、巴特的恩典概念(1945年)、奧古斯丁著作《反對學園派》(1945年)等幾十篇論文。這些歷史的視角應該能給當代的神學院學生和研究生提供鼓勵,使他們在經濟壓力、圖書館關閉、就業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仍然在疫情期間致力於學習。
路易斯指出,在戰爭這樣的時代,有三個「敵人」會對學者興風作浪:騷動不安、氣餒和恐懼。
一、騷動不安
第一個這樣的敵人是「騷動不安」,路易斯的意思是「本打算琢磨本職工作,卻琢磨了戰爭,爲戰爭動情」(59-60頁)。也就是說,學者會因爲當前的危機而分心,不能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學術追求中。今天,「騷動不安」的危險表現爲專注於社交媒體,不斷地滾動微博和搜索著谷歌,關注著華盛頓、倫敦或約翰內斯堡的冠狀病毒確診病例數、危險的經濟形勢以及政治動盪狀況的最新消息和分析。這對學術研究來說並不是一個明顯的敵人,我們很自然會想要了解時事的最新情況。然而,這種「騷動不安」或分心會阻礙我們追求卡爾·紐波特所說的《深度工作》——本該全神貫注,將我們的認知能力推向極限的態度。心無旁騖的工作可以磨練我們的能力,並利用我們的專注和精力去創造真正的、持久的價值。比起分析希伯來語語法、發展哲學證明或閱讀密密麻麻的清教徒散文,發微博和在頭條新聞中游逛要容易得多。
路易斯提醒我們,「我們的工作有大量敵手」(60頁)。新冠病毒並沒有創造出「刺激」的敵人——它只會加重我們的癖好。早在最近的新冠病毒爆發之前,人們就已經花了太多時間消費社交媒體和觀看CNN的「突發新聞」。對此,託尼·瑞科(Tony Reinke)寫道:
分心對人類的誘惑在每個時代都存在,因爲分心讓我們很容易從沉默和孤獨中逃脫出來。這讓我們認識到我們的有限性,認識到我們不可避免的死亡,以及上帝與我們所有慾望、希望和快樂的距離。
我們渴望那些看起來直接、帶來刺激和與自己相關的東西,我們常常太願意從需要我們深度專注的工作中脫離出來,因爲這些工作讓人感覺乏味或平凡,這些工作也讓我們錯過朋友的狀態更新或最新的今日頭條。路易斯提醒說:「倘若我們縱容自己,我們將會一直坐等這份心事或那份心事完結之後,才能真正安心本職工作。」(60頁)學習一門古代語言,或者寫一本專著或一篇論文,從來沒有真正的最佳時機。我們必須追求知識和學術研究的工作,即使在條件似乎不合適的時候,因爲 「有利條件永不會來」(60)。我們可以效法以薩迦支派的覺悟和決心,他們「通達時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代上12:32)。爲了正確看待我們現在的環境,「我們需要對過去有深入的了解」(58)。因此,不知道如何在疫情中帶領教會的牧師,可以從前幾代的基督徒如何應對流行病和瘟疫中有所學習。
二、氣餒
挫折或焦慮是學者們必須面對的第二個敵人,也就是「感到我們沒時間完成學業」(60頁)的那種氣餒。牛津大學的本科生和其他聚集在一起聽路易斯1939年演講的人,他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戰爭的前線。他們擔心德國的空襲,經歷了戰時停電和紙張短缺的挑戰。路易斯的理由是:「要是父母把我們送到了牛津,要是祖國容許我們待在那裡,那麼,這就是顯見證據,表明至少在當前,求學生活最有可能榮耀神。」(56頁)
學者們永遠不會完成他們渴望寫的每一本書和每一篇文章,牧師們很可能在完成他們計劃的系列佈道之前就退休或死亡。維吉爾(最偉大的羅馬詩人)在完成他的史詩作品《埃涅阿斯紀》前於公元前19年去世。同樣,簡·奧斯汀、狄更斯、卡夫卡、馬克·吐溫等無數作家都留下了未完成的小說。人們還想到了「美國神學家」愛德華茲,他在完成其偉大鉅著《救贖工作史》(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之前就去世了;而偉大的聖經學者萊特福特(J. B. Lightfoot)所留下的大量《約翰福音》、《使徒行傳》、《哥林多後書》和《彼得前書》詳細註釋在他死後一個多世紀才被人發現並獲得出版。
路易斯提醒我們:「未來就在上帝手中,不管我們交沒交給祂。無論和平與戰爭,切莫將你的美德或快樂寄託在未來。只有不大在乎長遠規劃卻每時每刻做什麼都是像『給主作的』那些人,工作才最快樂。神只鼓勵我們祈求日用食糧。履行義務或接受恩典的唯一時刻,是現在。」(61頁)因此,我們不應該像那個把主人的錢藏在地裡而不去投資的愚昧僕人一樣,以不作爲來回應「氣餒」這一的敵人(馬太福音25:18,24-27)。同時,我們必須防備雅各警告我們的驕傲自大,認識到當我們報名參加一個學位課程、計劃一個系列佈道會、或簽下一本書的合同時,我們必須謙卑地承認:「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雅各書4:15)
三、恐懼
恐懼是那些戰爭時期學習的人所面臨的第三個敵人。「戰爭以死亡和痛苦威脅我們,」然而路易斯敦促我們記住,戰爭「並未使死亡機率增高;我們百分之百都會死,這一比率不可能再高。」(61頁)。戰爭(或者說冠狀病毒)可能會影響死亡的原因或時間,但不會改變死亡的確定性。事實上,世界大戰或瘟疫流行的危機迫使我們「記起」死亡,「常常意識到自己之必有一死」(62頁)。世界衛生組織從2020年1月21日開始每天發佈有關新冠病毒的情況報告,剛開始只有282例確診病例;4個月後,全球病例數超過600萬,報告死亡人數37.5萬。這些膨脹的數字令人震驚和清醒,然而也提醒我們一直以來的事實:我們是凡人,我們都會死。認識到我們「不是來這裡永生的」,其實促使我們今天可以更充分地爲他人和上帝而活。作爲生活在不確定和不正常時代的生物——因爲任何時代都是不確定或不正常的——路易斯挑戰我們謙卑地把我們對學習的追求獻給上帝,作爲「通往我們此生以後希望樂享的神聖實存和神聖之美的一條道路」(63頁)。
摩西在詩篇90篇中有力地面對我們自己的死亡,並爲我們提供了需要的智慧。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作爲受造物的有限——「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並對我們的造物主說:「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第2,10節)無論我們今生面臨武裝衝突、新冠病毒,還是其他的勞苦和麻煩,我們都要禱告:「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12節)我們的日子已經被但以理所說的「亙古常在者」數算過了。考慮到我們作爲凡人的有限壽數,我們請求永生神在我們所有的日子裡使我們感到快樂和滿足,然後「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14-15、17節)。
這一結尾的禱告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基督徒學者在戰時仍致力於研究的信靠和決心,也表達了所有基督徒所有的決心:自己「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Scholarship in a Pandemic? A Lesson from C. S. Lew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