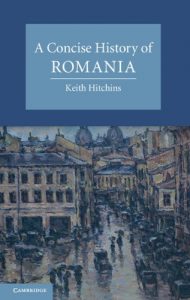 今年早些時候,我閱讀了凱斯·希金斯(Keith Hitchens)所寫的《羅馬尼亞簡史》(Concise History of Romania)一書,我讀這本書的原因只是很想更多了解那個我曾經稱之爲「祖國」的地方,而且我也希望讀這本書能夠幫助我在和歌麗娜以及其他羅馬尼亞朋友聊天的時候顯得不那麼無知。
今年早些時候,我閱讀了凱斯·希金斯(Keith Hitchens)所寫的《羅馬尼亞簡史》(Concise History of Romania)一書,我讀這本書的原因只是很想更多了解那個我曾經稱之爲「祖國」的地方,而且我也希望讀這本書能夠幫助我在和歌麗娜以及其他羅馬尼亞朋友聊天的時候顯得不那麼無知。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共產黨人在1940年代中期是如何讓一群崇尚自由的歐洲人臣服於一個後來持續四十多年的極權體制的?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順便給大家一些背景知識:羅馬尼亞的末代國王米哈伊一世仍然健在。(本文寫作於2014年,米哈伊一世已經於2017年12月5日在瑞典逝世。——譯註)我仍然記得和老一代的羅馬尼亞人聊天時,他們總能回憶起共產主義時代之前他們如何享受了二十多年的自由。要了解羅馬尼亞的共產主義統治是如何結束的,你可以讀這篇文章。)
題圖是我的妻子歌麗娜在羅馬尼亞奧拉迪亞讀小學時的全班同學照片。前排左起第七位就是她,他們的後面牆上就是當時的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的照片。
共產主義是如何佔領羅馬尼亞的呢?我們不能忽視強權和暴力的作用,自從羅馬尼亞共產黨奪得政權之後,無孔不入的羅馬尼亞祕密警察(Securitate,羅馬尼亞語的「治安」)在把反抗降到最低這件事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但更有意思的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透過聚焦於三個領域的革命而達成目的的。在每一個領域,共產黨都竭力地想要重寫羅馬尼亞的故事,這樣他們的觀念和理想才能被當作是羅馬尼亞人民對自由和平等的希望和夢想。下面就是他們所做的。
 爲了重寫羅馬尼亞歷史,共產黨首先要對付那些對羅馬尼亞的過去和現在持有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希金斯在他的書中解釋了這一過程是怎樣發生的。隨著革命的不斷進展,知識分子們(尤其是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被邊緣化,他們被「丟在一邊,在職業上無法發展。」他們沒有被投入監獄,但是他們被忽視、被邊緣化了,這是一個逐漸的過程。
爲了重寫羅馬尼亞歷史,共產黨首先要對付那些對羅馬尼亞的過去和現在持有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希金斯在他的書中解釋了這一過程是怎樣發生的。隨著革命的不斷進展,知識分子們(尤其是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被邊緣化,他們被「丟在一邊,在職業上無法發展。」他們沒有被投入監獄,但是他們被忽視、被邊緣化了,這是一個逐漸的過程。
隨後,在大學和其他研究機構,黨委和負責人要求教職員工在思想上統一、高度讚揚現政權的偉大,並重寫羅馬尼亞的過去。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因爲他們的信念而被投入監獄,但是他們被噤聲了。所以如果你對某個觀點持有與當局不同的想法,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被排除在外,在社會事務上你不能再發言。
下一步就更戲劇化了,那些堅持「橫在發展道路上螳臂當車的反動分子」,希金斯寫道,「就遭到更嚴厲的處理。」那些膽敢批評人類與社會繁榮新願景(即共產主義藍圖——譯註)的知識分子被罰款、被恐嚇,有時以煽動顛覆的罪名被投入監獄。只有一種知識分子能夠在新時代生存下來:那些認可共產黨政權現代化藍圖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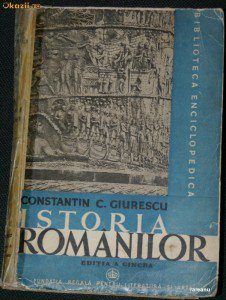 下一步,共產黨專注於研究和重新詮釋羅馬尼亞歷史。希金斯解釋說:
下一步,共產黨專注於研究和重新詮釋羅馬尼亞歷史。希金斯解釋說:
黨規定歷史研究要按照蘇聯模式進行,於是要求歷史學家們致力於證明馬列主義(有的時候也包括斯大林主義)歷史發展模式的正確性,因此歷史研究要專注於歷史中的經濟力量和階級鬥爭。藉此,黨內精英們對歷史的理解,首要的乃是反映當下政治利益的需要。於是,毫不令人驚奇,羅馬尼亞的過去,從達契亞(古羅馬尼亞王國——譯註)和古羅馬時代,直到今天二戰後的歷史,都必須在這一基礎上被重構。
在這一史學重構的過程中,被引入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重新解釋斯拉夫人在羅馬尼亞人種族與文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也重新描述了各公國和羅馬尼亞王國與沙皇俄國及蘇聯之間的關係。羅馬尼亞歷史上與西方的聯繫被故意弱化,這是這種新史觀不可避免的結果。
當歷史被重寫的時候,人心也被重寫了。
很遺憾,在這一革命中,歷史事實和邏輯辯論不再重要,研究歷史不再是爲了理解過去,而是成爲塑造未來的工具。希金斯繼續寫道:
黨也竭力地打壓開放、公開的對歷史發展中基本問題的討論,甚至不允許探究在某個歷史時刻究竟發生了什麼。只有一個歷史真理,而且這一真理也常常被修改以滿足黨當前的需要。
爲了加強新史觀的影響,黨控制了所有的歷史研討,並打壓所有與黨的歷史進步觀不同的人。他們是這樣做的:
黨自然不會把「新史觀」的出現交給偶然的機運。爲此,黨爲其目的改造了歷史學家這一職業群體,對這一類的知識分子進行嚴密監控……歷史學家被分派到不同的課題小組,對某個與黨的意圖相關的議題進行研究。……那些不能適應這種新的研究方法,或者厭惡這種「發現歷史真理」方法的老一輩歷史學家和年輕研究人員都遭到了孤立與邊緣化。
隨著時間的流逝,羅馬尼亞的歷史作品一次次地改版,以展現現政權是多麼地「在本質上是早先『進步力量』抗爭的自然積累,推動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社會正義。」希金斯用加強的語氣宣稱:「連死人都被改造成符合他們的結論」,並進一步解釋了在官方史書中羅馬尼亞的英雄——如米哈伊·愛明內斯庫(19世紀羅馬尼亞民族詩人——譯註)和卡拉賈萊(19世紀羅馬尼亞劇作家——譯註)是如何「在主流真理的光照下重新得到詮釋」的。
 還有一個擋住共產主義發展道路的團體就是教會。於是(一點都不令人驚奇地)共產黨實施了一系列政策,以「從社會中清除所有有組織宗教的影響,把羅馬尼亞轉變爲一個純粹的世俗國家」。
還有一個擋住共產主義發展道路的團體就是教會。於是(一點都不令人驚奇地)共產黨實施了一系列政策,以「從社會中清除所有有組織宗教的影響,把羅馬尼亞轉變爲一個純粹的世俗國家」。
爲什麼高層對宗教那麼反感呢?希金斯解釋說,因爲宗教「是一套在人民整體中具有深厚根源的不同意識形態」。教會就是一個對「社會進步」「不可避免的阻礙」。
他們如何處理信徒對黨所構建的藍圖所發出的質疑呢?他們扼殺了教會在政府允許的範圍之外參與社會生活的一切能力。他們關閉了教會開設的小學和中學,他們也關閉了教會下屬的慈善機構。
人民仍然有信仰自由,但是這一信仰自由被侷限於在家中、在教堂裡或者神學院裡的宗教學習。宗教被看作是「個人事務」,在公共領域裡毫無地位。
很多福音派和正教基督徒意識到了這些變化,並開始公開地抵制。但也有一些基督徒認爲,官方的「進步精神」可以和基督教信仰共存。
查士丁尼·馬林那(Justinian Marina)是羅馬尼亞正教的牧首,他留下了一份喜憂參半的遺產。他一方面竭力地保護信徒免遭逼迫,另一方面也發表作品呼籲信徒「適應新時代」,並且爲建造新社會而做出貢獻。查士丁尼深信這樣做符合正教傳統,希金斯這樣寫道。這位牧首想要協調共產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的衝突,以使兩者能夠互相受益。結果是什麼呢?自然是共產主義得勝和基督教在社會上被邊緣化,而同時,信徒的數量卻在社會和政治的雙重壓力下蓬勃增長。
我被羅馬尼亞基督徒在共產主義專制下的見證深深激勵。雖然他們當中有一些與當局合作、在信仰上妥協,但是更多的人寧願受苦也要對自己的信仰保持忠心。
「殉道者之聲」的創始人理查德(Richard Wurmbrand)看到當時不少的宗教領袖屈從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公開地讚美新社會的發展。他的妻子莎碧娜卻爲這樣的妥協感到噁心,告訴他要「堅強站立,洗去他們潑在基督臉上的羞辱。」理查德這樣做了,他勇敢地傳道,因此在監獄裡度過了很多年。
是什麼讓這些基督徒繼續地對聖經忠心,並且持守他們從先輩那裡領受的信仰?他們知道自己所在的是怎樣的時代。他們活出了一個不一樣的見證,他們沒有被共產黨對歷史著作的修改或是對知識分子的逼迫所勝過。他們屬於教會,而不屬於任何政治團體,並且他們相信神將來必會爲他們復仇。
今天,共產黨編寫的歷史書和他們關於「不斷進步」的幻想都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而教會卻在繼續前進,因爲教會依靠的是一本我們無法修改的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