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經常閱讀教會方面的書籍,你會發現,一些基督徒作者熱衷於談普世教會,另一些則更關注地方教會。
兩派的人都會反對這種劃分,他們會說:「不,不,我也談地方/普世教會。」但我指的是側重點——這種偏重會體現在講道時長、文章篇幅,甚至連感嘆號的使用頻率上。
從傑拉德·佈雷(Gerald Bray)的新作《教會:神學與歷史視角》(The Church: A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來看,他顯然屬於前者。在書的後半部分,尤其是在提出建議的章節中,他反覆抨擊宗派特色和神學上的「吹毛求疵」。在佈雷看來,當今教會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分裂。
而我這樣的人,大概會被佈雷認爲是有點太注重宗派了。不過,我想說的是,甲之吹毛求疵,乙之適度修剪也。
不過,這確實是一本好書,值得我用兩篇書評的長度來分享我的看法。一方面,佈雷的著作值得概述;另一方面,我也想指出像他和我這樣的人之間更大的差異,以及雙方立場各自可能帶來的隱患。我認爲,這樣做不僅能幫助讀者了解《教會》這本書的特點,同時也是對佈雷的公平對待,當然,我也要坦誠地表明自己的立場。
我先說第一部分,算是第一篇書評——概述。《教會》是否屬於神學院書店的系統神學部分或教會歷史部分?答案是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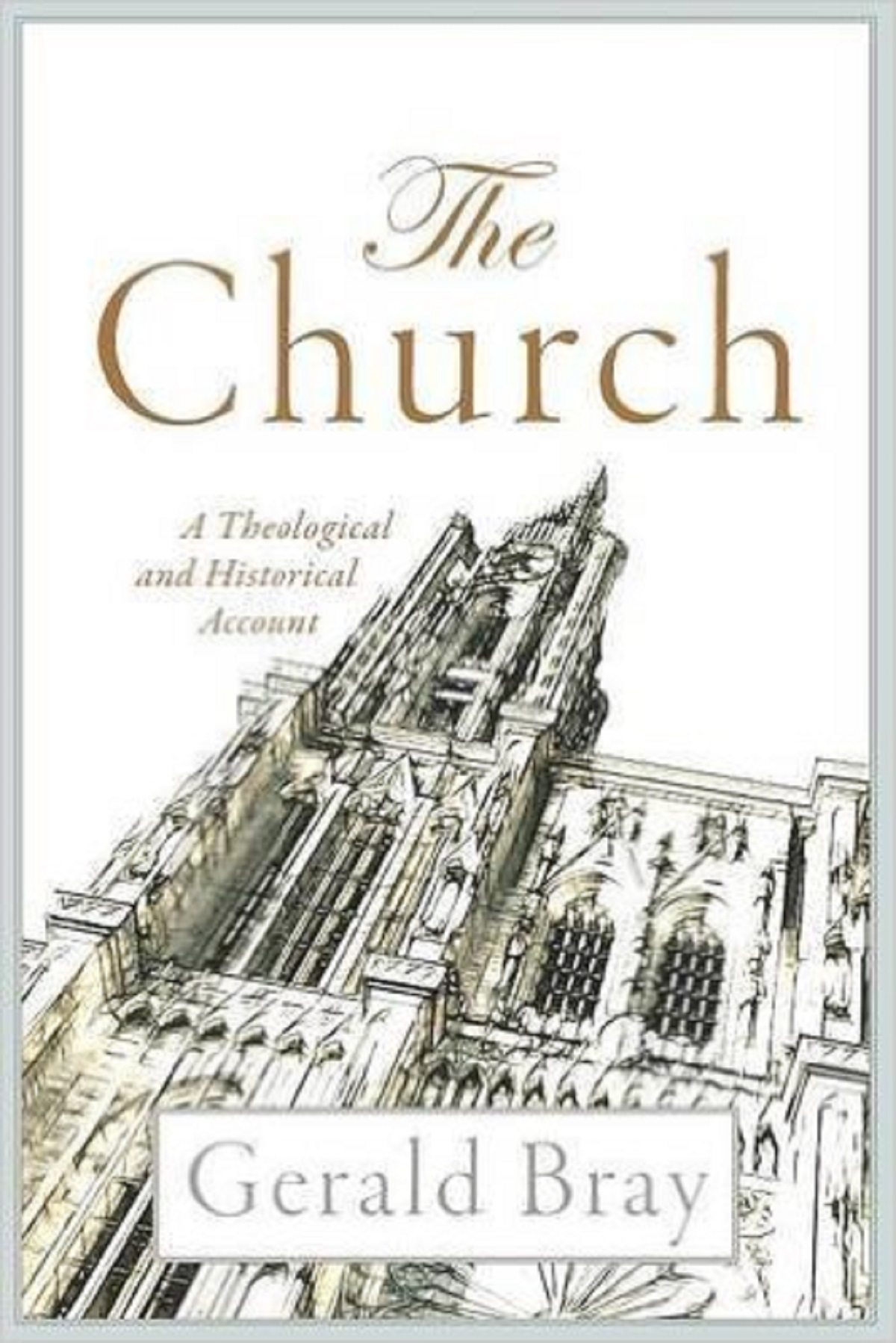 《教會:神學與歷史視角》(The Church: A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教會:神學與歷史視角》(The Church: A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傑拉德·佈雷(Gerald Bray) 著
貝克學術出版社(Baker Academic),288 頁
這本書讀起來像一部歷史著作,它按時間順序梳理了兩千年的教會歷史。第一章探討猶太教和舊約的淵源,第二章研究新約教會,第三至六章則依次討論了遭受逼迫時期、帝國時期、宗教改革時期以及改教後的教會。
雖然本書行文像歷史書,但它的目的是闡述教義並提出建議。從根本上說,這是一本關於教會教義的著作——用神學院的專業術語來說就是「教會論」。在討論宗教改革之前的章節,每章結尾都有一個小節總結教會教義的要點。而之後的章節則探討了基督教世界的教會論是如何在宗教改革後,像三角洲中的河流一樣分散開來。最後一章(第七章)則就如何制定教義和教會實踐提出了建議。
作者佈雷既是聖公會牧師,也是比森神學院(Beeson Divinity School)的教授。他在全書中都以教會的四個傳統標誌——合一性、聖潔性、大公性、使徒性——來闡述他的教會論。舉例來說,在宗教改革之前,「合一性」被理解爲制度層面的統一,「使徒性」則被認爲取決於主教的傳承。到了宗教改革時期,這兩個概念都發生了變化:「合一性」轉變爲屬靈層面的合一,「使徒性」則轉變爲教義方面的傳承。
總的來說,這本書講解教會教義的方式,不像化學教科書那樣按部就班——先給出正式定義,然後逐條列出各個章節要點。讀起來反而更像是一場關於新話題的整夜長談。在閱讀過程中,你會了解到許多有意思的歷史知識:比如居普良(Cyprian)是誰?教會法是什麼?彌撒、懺悔和煉獄等觀念是從哪裡來的?爲什麼新教特別重視信條?但作者提供這些歷史知識,是爲了引出更深層的教會論討論:教會是新以色列嗎?舊約的以色列是否就是舊約的教會?改教家們是如何看待教會與政府的關係的?教會的聖潔性究竟是什麼?
佈雷指出,在宗教改革時期,新教神學家們開始有意識地建構教會教義。這是因爲他們既要區別於羅馬天主教,又(很快)需要彼此區分,所以必須爲他們共同的組織生活下個定義。佈雷甚至認爲教會教義是宗教改革的「核心」(第 165 頁)。對於像我這樣比較「宗派化」的新教徒來說,這種說法可以有兩種理解:他是在說福音本身在宗教改革中並不是關鍵的爭議點,因爲雙方都持有福音(如果是這樣,我不同意)?還是說教會教義預設了特定的福音,所以談論一個就等於談論另一個(這點我同意)?這一點我也拿不准。
說到這裡,讓我多說幾句,因爲我覺得這反映了一個更大的問題。整本書對羅馬天主教的地位,以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是否在福音上合一這個問題,顯出異常的——或許是刻意的——沉默。這其實是把歷史敘述和教義闡述混在一起的風險所在。因爲我們很難分清,作者什麼時候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說話,什麼時候又是以神學家的身份發言。
作爲歷史學家的佈雷把羅馬天主教視爲基督教傳統中的一支——從歷史和描述的角度來說這很合理,就像人們出於純粹描述的需要會提到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人的「教會」一樣。但作爲神學家的佈雷對羅馬天主教的態度又是什麼呢?這一點並不明確。他表達了對教皇制度的異議,也指出羅馬天主教在馬利亞永貞等新內容上「背離了使徒性」(第 241 頁)。但他會不會認爲羅馬天主教已經背離了使徒的福音呢?對此他並沒有明確表態。
我之所以在這個細節上多費筆墨,是因爲這有助於我們在普世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光譜中定位《教會》一書,也揭示了本書最關注的問題。
當佈雷審視那些自稱爲基督教的群體時,最令他擔憂的是宗派的混亂。他認爲,堅持自己的宗派特色是造成這種狀況的部分原因:「基督徒合一最難以體現的地方,就是在宗派架構和事工層面」(226 頁)。我們當中有太多人——在這裡我想佈雷指的是像我這樣的浸信會信徒和保守派路德宗信徒——採用的信仰告白「聲稱是基於新約,但實際上通過堅持某些特定立場(比如關於洗禮的立場)而超出了聖經範圍」(241 頁;另見 224 頁)。不過,威斯敏斯特傳統的信徒也難辭其咎。他們的神學家知道「他們的宗派立場過於僵化和排他」,不得不爲「他們明知最多只是次要的信念」辯護。但他們仍這樣做,是因爲「許多保守派擔心,一旦開始修改像威斯敏斯特信條這樣的歷史性信仰宣言,就不知道這種改動會止於何處」(241-242 頁)。
因此,總的來說,「保守派新教神學家們……常常躲進誇大的宗派主義中,人爲地重提 16、17 世紀的爭論,或是陷入吹毛求疵的爭議中」(237 頁)。在本書的最後幾章中,佈雷反覆以合一作爲評判各種問題和趨勢的首要標準。比如,他認爲女性按立的議題之所以是令人遺憾的,是因爲它「給教會合一又造成了一次打擊」(245 頁)。
在佈雷看來,解決之道在於推進對基督徒在福音裡的合一性和大公性的更深理解:
「新教徒,尤其是福音派信徒,能否超越這些困難,對福音的大公性有新的、更深的理解,從而擁抱一個完整的神學和社會願景,這還是個未知數。但……這是他們當前面臨的最緊迫的考驗。」
他認爲我們在當代世界的基督教見證取決於此(237 頁)。只要你理解了這些(關於教會合一和普世性的)擔憂是如何驅動佈雷和《教會》這本書的立場,你就能理解爲什麼談到羅馬天主教時,他保持沉默了。
說到這裡,就引出了第二篇書評。佈雷對羅馬天主教保持沉默,以及他對宗派特色的不以爲然,幫助我們看到福音派群體中存在的一個明顯分化。爲了便於討論,讓我們假設所有相關人士都是持守相同福音的福音派基督徒。他們在理解和強調的重點上形成了兩極:一端是那些強調普世教會的人,另一端則是那些強調地方教會的人。
強調普世教會的基督徒,往往把文字和熱情投入在強調福音裡的「合一性」和教會的「大公性」這兩個特徵上。也就是說,他們傾向於普世教會合一的方向。他們對那些引發基督徒爭論的話題(比如教會治理)以及代表這些分歧的宗派缺乏耐心。他們強調解經式講道、教導和門徒訓練的重要性,而對地方教會的聖禮持比較寬鬆、開放和非特定的態度。他們可能會支持地方教會及其紀律,承認教會對基督徒成聖很有幫助:「這會幫助你成長!」但這從來不是他們寫書或主日學課程的重點,有時甚至感覺只是敷衍了事。(例如,佈雷在最後一章專門用了一節來建議實行教會紀律,但他沒有給出任何積極的、建設性的指導。相反,他用整章來批評教會紀律的歷來使用方式,220-221 頁。)在最健康的狀態下,強調普世教會的人善於把首要之事放在首位,讓人關注得救所必需的事。但在最不健康的狀態下,他們可能偏向普救論和廉價恩典。
強調地方教會的基督徒則在主日學課程和博客文章中,更多談論福音對「聖潔」的呼召和忠於「使徒」教義這兩個特徵。他們也談論得救所必需的事——福音,但他們在定義福音時更加謹慎(第一群人會說太過謹慎)。不僅如此,他們承認像教會治理這樣使基督徒產生分歧的問題對得救來說並非「必需」,但他們認爲這些事項對於把福音傳給下一代仍然「重要」,而且是聖經所命令的。當然,風險在於他們在評論區討論次要問題時,可能會忘記他們在更基本的福音上是合一的。他們強調地方教會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爲它有益處,更是因爲這是耶穌的命令。他們也談論講道和塑造性的管教,但在解釋聖禮和實施糾正性管教時會更加嚴格。如果不加節制,這一端會演變成宗派主義、地方主義、偏激、不健康的獨立性和律法主義。
強調普世教會的人更多談論福音中的陳述性真理——神爲我們做了什麼。強調地方教會也談論這些真理,但更多強調基於這些真理的實踐要求——我們應該做什麼。
強調普世教會的人傾向於把教會定義爲一個團契或奧祕的交通(借用艾弗里·杜爾斯樞機主教[Avery Cardinal Dulles]的分類)。比如佈雷寫道:"無論教會是什麼,它的核心仍然是由那些從神的靈重生的人組成的群體"(第 216 頁)。強調地方教會的人傾向於把教會定義爲基督統治的前哨或一個制度(再次借用杜爾斯的分類)。因此我一再把地方教會比作「大使館」(參見《政治性教會》Political Church [書評]),而且傾向於用制度性的語言來定義它,比如:」教會是一群基督徒,共同認同自己是耶穌的跟隨者,他們定期奉主的名聚會、傳講福音\舉行聖禮。」(《理解會眾的權柄》Understanding the Congregation’s Authority,38 頁)
強調普世教會的人更傾向於稱自己爲「福音派」,而強調地方教會的人則更傾向於稱自己爲浸信會、長老會或路德宗。
話雖如此,不同的宗派傳統往往會偏向其中一方。福音派(低教會)聖公會傾向於強調普世教會;而美南浸信會和美洲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則強調地方教會。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據此劃分基督教出版社和各個會議。
強調普世教會的人更可能從所謂的福音派公共領域(包括書籍、博客、會議、音樂節)汲取屬靈養分。而強調地方教會的人則從自己的教會或其宗派資源中獲取養分。
人們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爲:強調普世教會的一方會使用教會外機構,而強調地方教會的人不會使用教會外機構,但這種說法可能並不準確。事實是,強調普世教會的人傾向於使用那些可能會取代地方教會功能的教會外機構(比如各種校園事工)。強調地方教會的人傾向於使用直接支持地方教會工作的教會外機構(比如宗派架構),但這樣做可能會使他們失去接觸更廣泛基督身體(即普世教會)資源的機會。
這種分類只是一種思考工具,無法完全公平地描述任何一方。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這兩方面都很重要。但我認爲,說某些作者的側重點更偏向這一端或那一端並非誇大之辭。我相信佈雷和我持守相同的福音,但我們可能相差一兩個點,我偏向地方教會這邊,他偏向普世教會那邊。當然,我們每個人都認爲自己的立場是平衡的。佈雷認爲他很平衡,我認爲我很平衡,樂馬可和克里斯托弗·萊特(Christopher Wright)也認爲他們很平衡。
事實上,我們都可以在這些方面做得更好:更完全地順服神的話語,更好地領受福音的真理和命令,更好地作爲聖靈充滿的群體和基督國度統治前哨的教會。我很贊同樂馬可的平衡之道:他建議在不同宗派之間保持界限清晰但不要太高,並經常越過籬笆握手。我既需要九標誌強調的地方教會特色,也需要福音聯盟或爲福音同心(Together for the Gospel)所確認的普世教會特質。
根據我的觀察,不同的福音派群體往往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立場。代際差異似乎也是一個因素(這也是我的直覺)。我認爲福音派的嬰兒潮一代和較年長的X世代相比他們的基要主義父母更偏向普世教會(我沒有統計數據支持這一點)。但一些較年輕的X世代和千禧一代卻在向地方教會方向推進。
從神學角度思考,我認爲至少有一個關鍵問題會推動你向這一端或那一端傾斜:你是否認爲聖經爲教會治理或架構提供了具有道德約束力的規範?也就是說,聖經是否告訴我們應該採用會眾制、長老制還是主教制?
傾向普世教會者經常主張,聖經對教會如何組織架構幾乎沒有任何約束性規範。佈雷再次提到:
據我觀察,大多數低教會福音派聖公會信徒都承認,主教制並非源自聖經,而是早期教會的一項創新——只不過經過幾個世紀的實踐證明它確實有用。因此,我們不妨繼續保持這種制度。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是歷史實用主義者。
而偏向地方教會的人則認爲,教會治理其實只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可以稱之爲社會倫理。除非你認爲新約中的所有倫理規範都不適用於今天,否則我們就必須通過更細緻的解經工作,來確定聖經中哪些倫理和治理規範對我們仍然具有約束力,哪些則已不再適用。
與佈雷的觀點相反,我寫道:「某些組織事務可以根據具體環境靈活調整,但教會秩序的基本原則與福音信仰是密不可分的」,這些原則都是有聖經依據的(《不要開除你的教會成員》〔Don't Fire Your Church Members〕,15 頁)。我們的福音秩序(這裡指的是教會的治理結構)是從福音信仰中自然生發出來的。對於福音本身,以及爲了展現和護衛福音而設立的福音秩序,聖經都提供了充分的指引。
就像在我在《理解會眾的權柄》(Understanding the Congregation's Authority)中所說:
福音與福音秩序之間的雙向關係是一個良性循環,這個模型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不同立場對福音和教會秩序關係的理解差異。
一個人對教會治理的立場會如何影響他在教會論光譜上的位置(靠左或靠右)呢?如果聖經確實爲教會的本質和治理方式提供了道德規範,那麼每個基督徒都必須順服這些合乎聖經的架構。如果沒有,我們與地方教會的聯繫就會變得鬆散。參與教會將不再由聖經的命令驅動,而是由個人對屬靈需要的判斷來決定。如果任何教會架構都可以,那麼嚴格來說,只要能實現架構的目的,沒有架構也可以。如果你能在地方教會之外滿足屬靈需要(團契、教導、敬拜和類似長老的指導),爲什麼不呢?這樣看起來,似乎基督教真正的「戲碼」是屬於那些認爲自己可以獨立於地方教會而運作的基督徒。我們都是自由人。
(很可能佈雷確實認爲教會架構中的某些事項是聖經要求的,比如長老是否有權柄?教會是否該施行管教?這意味著,當他反對有一個新約模式時,他可能就自相矛盾了。)
這裡不是深入討論聖經是否決定我們教會秩序的地方。但這就是爲什麼當佈雷和我有這樣的分歧時,我會說:如果你想了解教會論的歷史,那麼可以讀他的書;但如果你想爲福音派尋找教義和事工的前進方向,那就不必了。
令人欣慰的是,佈雷和我都確認,我們加入地方教會最終並不是出於功用性或命令性的考慮。我們加入教會的呼召最終植根於福音的宣告。正如佈雷所說,我們加入教會是因爲這是「基督徒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教會是我們的「首要群體」(249 頁)。也就是說,我們加入教會不僅是因爲這對我們有益處,甚至不僅是因爲這是命令,而是因爲這就是我們的本質——我們是基督的身體,是家人。感謝讚美主!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Are You a Universal Church-er or a Local Church-er?